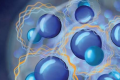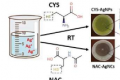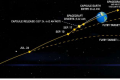对黑犀牛过去和未来的基因组见解
1960年至1995年间,激烈的偷猎导致野生种群数量减少98%,标志性的非洲黑犀牛(Dicerosbicornis)面临着不确定的未来。虽然目前数量在增加,但这种动物仍处于极度濒危状态。

黑犀牛历史上的活动范围覆盖了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大片地区,但如今仅存的黑犀牛只栖息在少数保护区。黑犀牛在其破碎的自然栖息地遗迹中的生存依赖于专门的保护工作。
发表在《分子生物学与进化》杂志上的一项新研究“消失的野兽的历史采样:黑犀牛的种群结构和多样性”重塑了我们对黑犀牛进化和自然历史的理解,为了解该物种的遗传打开了一扇窗过去,同时敦促我们开辟一条保护其的道路。
该研究描述了黑犀牛在上个世纪大范围崩溃之前和之后的种群结构和基因组多样性,为种群收缩期间遗传多样性如何形成提供了模型。
该研究的主要作者之一托马斯·吉尔伯特(ThomasGilbert)表示:“真正探索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使用具有良好记录的时间收集的物种,这些物种也与良好的人口统计记录相关。”“可悲的是,像黑犀牛这样的物种就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它们长期以来对大型猎物猎人和偷猎者具有吸引力。”
然而,根据共同第一作者BiniaDeCahsanWestbury的说法,这项研究的动机不仅仅是科学好奇心,“研究黑犀牛随时间的遗传史可以提供对其进化轨迹的重要见解,并有助于制定有效的保护策略。其剩余人口。”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作者对1775年至1981年收集的63个博物馆标本以及来自现代黑犀牛种群的20个个体进行了基因组测序,编制了迄今为止该物种最全面的遗传数据集,并显着推进了早期的研究工作。
该研究的另一位主要作者YoshanMoodley指出:“整个基因组序列揭示了黑犀牛中与保护相关的种群结构,比传统标记预期的要多得多。”他强调了尖端基因组技术的变革力量。
对数据的分析揭示了历史上存在的六个主要黑犀牛种群以及四个亚种群,从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精确地划分种群边界。值得注意的是,结果表明,更新世期间非洲的构造裂谷“推动了几个迄今为止未知的种群的进化,其中许多可能仍然存在于当今的肯尼亚集合种群中,”穆德利强调。
除了地理障碍之外,当这些基因流动的障碍暂时消除时,黑犀牛的进化史也是由二次接触塑造的。德卡桑韦斯特伯里说:“这些事件的相互作用导致了撒哈拉以南地区该物种因距离而出现显着的隔离模式。”他指的是地理上相距较远的种群也表现出更大的遗传差异的趋势。彼此。
研究人员进一步评估了黑犀牛历史和现代种群的近亲繁殖水平,这是对遭受严重种群瓶颈的物种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现代样本强调了人口收缩和随后的遗传漂变的深远影响,”德卡桑·韦斯特伯里指出,“南部非洲个体经历了最严重的影响,并且是所有人口中近亲繁殖程度最高的。”
该研究的作者表示,一些种群表现出殖民时期之前的近亲繁殖证据,这凸显了人类活动对该物种的长期影响。
总而言之,这项研究强烈呼吁采取行动,改善黑犀牛的保护和管理。
“长期以来,野生动物保护当局一直在努力纳入和实施紧急遗传建议,这损害了相关的生物多样性,”穆德利指出。他强调说:“对东非发现的新种群给予最高的保护优先权绝对是至关重要的。”这呼应了该研究对肯尼亚和坦桑尼亚黑犀牛进行全面基因检测的紧急呼吁。
此外,研究中确定的不同进化群体,例如鲁伍马、马赛马拉-塞伦盖蒂,以及可能的楚鲁国家公园亚群,应该成为单独管理的重点,以维持其独特的遗传谱系。
这项研究向已故卡迪夫大学教授迈克·布鲁福德(MikeBruford)致敬,他是保护遗传学领域的杰出人物,也是该项目的合著者。作者指出,他的去世“不仅对他的家人而且对整个保护生物学来说都是一场悲剧”。布鲁福德的遗产继续影响着这个领域,这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地球遗传遗产的保护的持久证明。
声明:本站所有文章资源内容,如无特殊说明或标注,均为采集网络资源。如若本站内容侵犯了原著者的合法权益,可联系本站删除。